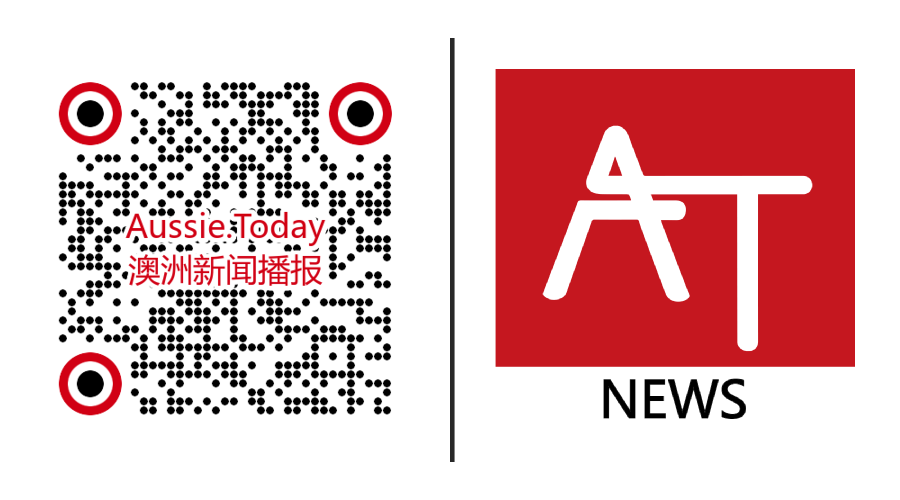女性政治家往往认为自己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女性,她们占据了舆论界的所有点。
当我为了制作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代表女士 “节目而与不同年代和不同政治信仰的女议员交谈时,我已经准备好让她们彼此意见相左。
但是在制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最让我震惊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经历。
事实上,许多妇女都提出了这一特殊观点,而且用词相同,几乎是喜剧性的。我们发现南澳的南希-布特菲尔德女士(自由党,1955年当选为参议员)在描述这一特殊经历时,与萨拉-汉森-杨的说法完全相同,后者是在半个多世纪后当选的,而且是为一个更进步的政党工作。
“当然,这也发生在我身上,”工党的王佩妮说。
“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前议长布朗温-毕晓普说。
让我们把它留给朱莉-毕晓普–联邦自由党历史上最资深的女性–来描述。
毕晓普女士是澳大利亚最近在联邦内阁中担任唯一女性的人。2013年,在总理托尼-阿博特担任副领导人期间,她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内阁由她和18名男性同事组成。
她加入了已故玛格丽特-吉尔弗约尔夫人和已故苏珊-瑞安等先驱者的行列,他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弗雷泽和霍克内阁中作为唯一的女性积累了许多年的经验。
毕晓普女士将这种现象称为 “性别失聪”。
“她说:”如果你是一个房间里唯一的女性,而你提出了一个想法或你说了一些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往往没有人回应。然后下一个人说话了。然后下一个人实际上占用了你的想法。然后桌子周围的所有男人都点头说,’多好的主意’。而你会在那里,’我不是说了吗?难道没有人听到我吗?”。
许多妇女说,她们与同事讨论了 “性别失聪 “的经历。澳大利亚第一任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说,提及这一现象是 “在我与女性交谈的所有经历中,有一个总是让人点头”。
“她说:”研究表明,尽管男性不认为他们这样做,但他们实际上占据了过多的谈话时间。”如果你有一个五个人的会议,直到其中四个人是女性,女性才会得到公平的谈话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以上的男人,那么他们将主导可用于讨论的时间。”
吉拉德女士提出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法:当房间里有超过一个人时,女性会在声音上相互支持。
“当然,你知道,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一旦你知道这一点,这是我在很多很多年里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互相支持。即使你不同意这个想法,至少也要对房间里的女人有礼貌地说:’嗯,正如安娜贝尔刚才所说的那样’,一旦变得清楚,一个想法就会被一个女人忽视。”
在《被代表的女士》的采访中,妇女们提出了各种策略,在她们是少数人的会议上,她们曾用这些策略使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布朗温-毕晓普的首选技术?”命名它。你必须要求它!我很高兴你同意我的观点!”
包括黄参议员在内的一些人赞同吉拉德女士的建议,即妇女应团结起来,相互关注对方的贡献,即使是她们个人不同意的贡献。
还有一个更令人沮丧的选择,如果更快的话;来自国民党、自由党、工党和绿党的妇女都承认,让一个政策想法启动和运行的一个方法是 “让那个家伙认为这是他的想法”。
“汉森-杨说:”预测他要说什么..

前自由党参议员阿曼达-凡斯通(Amanda Vanstone),典型地跳出了框框的思维。
她说:”如果你在一个有很多男人的房间里,议会中的大多数女性一般都会这样,还有另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在一个男人发言后表达某种气愤,说:’哦,我的天,这个房间里有太多的男性荷尔蒙’。
“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都去开始考虑他们的设备。而且,这意味着你有大约15秒的时间,他们正在寻找,’哦,她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说你想说的话了。你已经有了发言权。
“转移注意力!让他们想一些他们喜欢想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进去了。”
令人震惊的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年代的女性竟然能如此一致地描述在会议中发现自己听不见的经历。我以前就听说过这种现象,但听到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如此轻易地、不假思索地阐述这种现象,令人惊讶。
他们为绕过这一障碍而开发的技术和策略听起来很累:在已经涉及到仔细选择不会使你看起来太吵、太放荡或太傻的衣服,以及选择不会使你听起来太专横、太愤怒或太有野心的语气的精神负担中,又多了一个包袱。
有多少男性议员可以报告说,他们用一套类似的技术来武装自己,以便在他们在会议上发言而没有人听到的情况下进行部署?
有句老话说,金格-罗杰斯做了弗雷德-阿斯泰尔所做的一切,只是倒着穿高跟鞋,这句话对政治非常贴切。
女政治家做着男政治家所做的一切,只是对只存在于她们身上的隐藏陷阱有一种高度的、持续的感觉。不要向权力伸手,以免你显得野心勃勃或抓狂。

显然,在女性开始到来之前,澳大利亚的每一个议会都是以其自身的男性化节奏运行的。有趣的是,妇女在多大程度上将隔离自己到来的文化冲击的工作内在化了。
以伊尼德-里昂为例,她是第一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女性。在她的 “处女演说 “中,她向她的男性同事明确表示(通过一个令人放心的家庭形象),她不会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我知道,许多可敬的成员以接近惊恐的态度看待妇女进入立法大厅的问题,”她在1943年9月29日对议会说。
“他们担心,我毫不怀疑,新扫帚的使用有些过于激烈。我希望能让他们放心。我对扫帚和扫地持有非常正确的看法。虽然我很清楚,新扫帚对家庭主妇的工作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辅助工具,但我也知道,它在扫帚柜里无疑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把特殊的新扫帚知道,她有很多东西要向我不敢说这个特殊柜子里的人学习。
“无论如何,她希望自己的行为有足够的谦虚和对自己知识不足的充分认识,至少能赢得可敬的成员的愿望,向她提供他们可能给予的帮助。”
当琼-柴尔德–在1974年作为唯一的女性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接受采访–被问及她的决心有多大时,她回答说。”非常。”
当电视采访者追问她–“当你说你很坚定时,你认为你能表现得多坚定?”- 她的回答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阶段不太确定,”她小心地说道。”它看起来像具有攻击性,而这是男性目前的特征。”
自伊迪丝-考文是第一个进入澳大利亚议会的妇女以来,在过去的100年里,她们仔细观察了任何男人在进入政界时的假设:他有权被听到,他被允许有野心,如果他有孩子,没有人会质疑他在堪培拉时谁在照顾他们,人们认为他的妻子会照顾所有这些。
这些假设没有以同样不假思索的方式提供给妇女。
当我问罗斯-凯利–第一位以部长身份在众议院回答问题的女性–男人在政治上最理所当然的是什么,她回答说。

许多接受《代表女士》采访的女性表示,野心被认为是男性政治家的一个优点,但对女性来说是一个缺点。
朱莉娅-吉拉德,第一位担任总理的女性–像她之前的许多男性一样挑战她的党的领导地位–指出,在某些方面,她从未被原谅这种政治野心的行为,她不再是一个支持性的副手,而是把自己推到了最高职位。
但让我们回到这个可听性的问题上。
在确定了许多妇女都有相同的经历,即在她们发言的情况下,确实没有人听她们说话,那么,当她们要说的东西很危险或具有对抗性时,她们有时选择不说话,我们能感到惊讶吗?
今年2月,当年轻的联盟工作人员布列塔尼-希金斯(Brittany Higgins)披露她涉嫌在前一年的内阁部长办公室被强奸时,政治世界被颠覆了。
希金斯女士说,她当时没有告诉警方,因为她觉得这将给自由党带来政治上的尴尬和麻烦,而当时自由党正处于棘手的选举边缘。

我们很容易认为,她的沉默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她的初级身份:一个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年轻女人,被她上面的权力结构和眼前的利害关系所吓倒。
当然,希金斯女士后来证明自己是由一些相当严厉的东西组成的。但有趣的是,不愿意报告或投诉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待遇或骚扰,绝对不限于初级或无权的妇女。
朱莉娅-吉拉德说,她在担任国家首位女总理的初期选择不提及或不对抗对她的性别歧视待遇,因为她认为她的性别的 “新鲜感 “会逐渐消失。
2013年,当时的总理有礼貌地回避了电台主持人霍华德-萨特勒(Howard Sattler)就她的伴侣是否是同性恋这一话题提出的坚持不懈的问题,这段录像–今天来看–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肮脏的谣言会被如此不尊重地放在一位男总理面前吗?
吉拉德女士说,她当时不想陷入关于性别问题的耗氧交流中,因为她有太多其他想谈的事情。
绿党参议员莎拉-汉森-杨数月来一直无视男性参议员在会议厅里用她被认为与之有染的男人的名字对她进行猫叫,她这样做是因为她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使她感到不安。
在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妇女都采取了 “硬碰硬 “的政策,这与恐惧或缺乏机构或权力并不冲突。
布朗温-毕晓普没有时间让女性 “发牢骚”;她说,唯一的答案是要超越那些虐待你的人。
“我认为人们扮演受害者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女性,”阿曼达-凡斯通说。
“因为只要你说,’我是受害者’,你知道,’你找我麻烦,你对我很讨厌,因为我是个女人’,他们就赢了。你已经放弃了。”
然而,吉拉德女士以她的 “厌女症演讲 “惊人地放弃了这一技巧,而汉森-杨参议员最终通过法院起诉了一个折磨者,因为她认为参议院本身并不保护她免受工作场所的骚扰,而且她的沉默并不能使问题消失。
现实地说,没有一个女人是为了谈论自己或她所遇到的待遇而从政的。像所有的政治家一样,女性的政治资本是有限的,而且很少有人热衷于把它主要用在性别问题上。
对于政治保守派的妇女来说,情况特别复杂,因为政府的 “妇女问题 “现在成了党派辩论的焦点。工党–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在1994年采用的预选配额制度,在自己的队伍中实现了性别上的近乎平等的历史性成功–已经有效地殖民了这个问题。

对自己党内的性别歧视直言不讳的自由派女性现在不仅面临着所有女性都要权衡的风险(我是否会被相信,这是否会影响我的事业,关于我的故事是否会被传播,这是否会成为我被记住的原因),而且还面临着被指控为自己党内叛徒的风险。
前自由党议员朱莉娅-班克斯和毕晓普女士都面临着背叛党派的指控,班克斯女士对自己同事的批评很快就被指责为职场恶霸的低语运动。对内阁部长凯伦-安德鲁斯的类似指控是在她宣布对议会中的性别歧视文化 “深恶痛绝 “几天后出现的。
一位自由党议员告诉我,”作为保守派女性,我们传统上都是忍气吞声,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不符合主流评论界的性别说法”。
她说,她和她的同事们更愿意在幕后工作,而不是寻求头条新闻,并指出在COVID之前,性别薪酬差距在稳步缩小。
诚然,政治左翼的女性对在镜头前讨论性别问题更为开放。在为《代表女士》发出的参与拍摄采访的邀请中,所有礼貌性的拒绝都来自保守派或国家党背景的女性。
保利娜-汉森也没有同意接受采访–尽管有很多人找她。
莎拉-汉森-杨说,工党的女性并没有让她们的保守派同事的事情变得更容易。
“我认为自由党内的女性很难站出来,因为如果她们站出来,就会被政治对手利用。她说:”有一些政治观点要做,你知道,全面的。
“这就是政治。当然,我对这一点并不天真。但我想我已经忍受了很长时间……我是澳大利亚议会中的一名澳大利亚妇女,有些问题我们实际上必须更好地相互配合。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当另一方的女性成为攻击的对象,或者是,你知道的,运气不好的时候,不要只拿政治观点说事。”
你可以在今晚8点在ABCTV和iview上观看Ms Represented的第二集,你也可以在那里看到所有四集的视频。由Annabel Crabb和Steph Tisdell主讲的Ms Represented播客,可以在你获得播客的地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