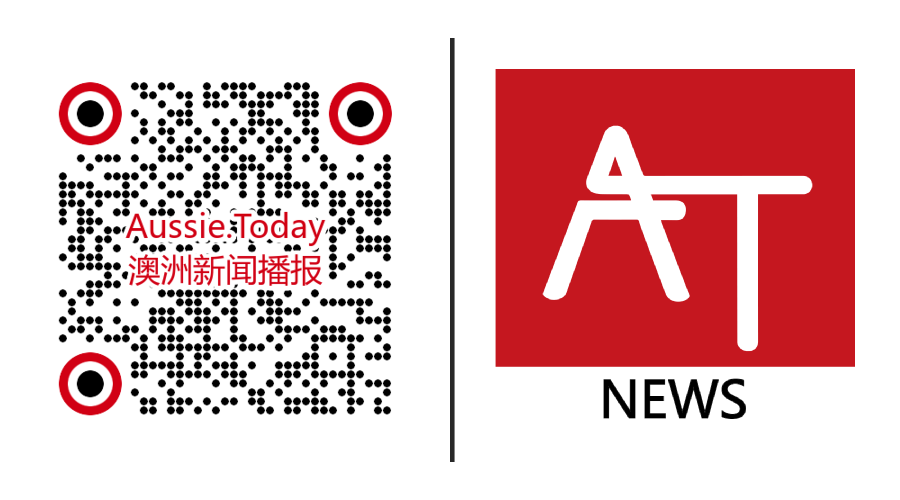那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视频电话,杰*回忆起它时仍会流泪。那是在深夜,杰伊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朋友Mhelody还活着。
“我看到她躺在背景的床上,背对着镜头,”杰伊说,并讲述了那次视频通话。
有人拿起了Mhelody的电话,一个杰伊不认识的人。Mhelody似乎没有反应。
“我记得他当时非常生气,大喊大叫。他确实说过,他将强奸Mhelody并给她带来艾滋病。”
警告。下面的故事包含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的内容是对抗性的。
在那次视频通话后大约8个小时,米洛迪被呛得不省人事。第二天,她就死了。
米洛迪-布鲁诺是一名来自菲律宾的25岁变性人,大约六周前来到澳大利亚寻求爱情。
里安-托耶(Rian Toyer)是一名与她约会的男子,他告诉警方,他在一次双方同意的性扼杀行为中意外地杀死了她,为此他被判了22个月的监禁。
托耶的认罪意味着他的过失杀人案直接进入宣判阶段,不需要进行审判。
某些证据从未在法庭上得到证明,包括杰伊对视频通话的叙述,尽管杰伊的兄弟向警方做了相关陈述。
背景简报》和ABC地区的联合调查发现了更多法院没有看到的信息,包括救护车日志、第一反应者的声明、医疗记录和尸检报告。
这些信息是否会对判决产生影响尚不得而知。
曾监督新州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刑事审判的前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惠利审查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收集的信息。
“不幸的是,我们对所有的细节了解得还不够,我们评论的是零星的片段,但它们都是相当重要的片段。
“把它们放在一起,我认为至少你可以说它们揭示了这是一个比法官设想的更严重的过失杀人案。”
米洛迪-布鲁诺在菲律宾马尼拉郊区的一个小房子里长大。

她的童年朋友艾拉记得他们如何吃芒果和 “冰糖”,并爬上米洛迪家的平坦铁皮屋顶。
他们对音乐和时尚有着共同的热爱。然后,在青少年时期,他们都转型为女性。
“[Mhelody]会播放响亮的音乐,我们会穿上女人的衣服,在这里做模特,”Airah说。
“我们会进行练习,并互相询问[选美]问题。”
米洛迪的母亲阿维利娜-布鲁诺(Avelina Bruno)回忆说,米洛迪在完成学业后在马尼拉独自闯荡,自己租了房子并寄钱给家里。
艾拉赫和米洛迪仍然是亲密的朋友。
“当[Mhelody]听到音乐时,我们会感到惊讶,她突然跳舞,然后我们都会笑,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Airah回忆说。
梅洛迪对选美活动非常关心。在一个宣传视频中,她说参加选美比赛不仅仅是为了获胜。
“我想传递一个信息,即[我们的]行业庆祝多样性和平等,我们LGBT也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出人头地,”Mhelody说。
虽然Mhelody在马尼拉的生活很充实,但Airah说她在寻找更多。

“她不想要一个菲律宾人,她想要一个外国人,”Airah说。
“如果是菲律宾人,她不会得到真正的爱,不像外国人,在那里你会感受到关怀和真正的爱,以及他们所说的在爱情方面的平等。”
来自新州瓦加瓦加镇的安迪,第一次通过一个国际约会网站认识了米洛迪。
他曾两次到菲律宾看望米洛迪,但基本上他们的恋情是远距离的。
梅洛迪会给他留下爱的信息。
“嘿,亲爱的,你怎么样?”她在其中一个问道。
“所以我刚刚下班回家,我只是想到了你,我不知道,我在想你。
“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爱你。”
在他们在一起近一年后,这对夫妇在2019年8月组织Mhelody来澳大利亚待了三周。
她住在瓦加郊外安迪的农舍,两人参观了悉尼和雪原。
但这段关系中存在着紧张。当安迪将米洛迪送到瓦加机场飞回家时,他承认他已经松了一口气。
他说:”这次的经历有点颠覆性,”他说。
“我非常迫切地想让她上飞机,然后说:’听着,再见,等你回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情况’。”
他们继续在网上聊天,安迪认为米洛迪一直都回到了菲律宾。
然后三周后,他收到了敲门声。那是警察。他们告诉他Mhelody已经在瓦加基地医院去世了。
安迪不知道的是,米洛迪没有回菲律宾的家。她有其他计划。
朋友们说她又去了悉尼,甚至去了昆士兰。
然后在某个时候,在安迪不知道的情况下,米洛迪回到了瓦加,和一个新的男人在一起了。
安迪很快就知道,警方已经指控一名男子涉嫌杀害米洛迪,这是她在同性恋约会软件Grindr上认识的另一名瓦加本地人。
这个人就是里安-托耶,他是空军的一名下士,在附近的皇家空军基地工作。
安迪参加了托伊尔在瓦加的旧砖砌法院的每次出庭宣判,”只是为了有一个证人,你知道,代表米洛迪,”他说。
有的时候,安迪想揍托耶。有时他会因冷酷的愤怒而颤抖。
法院接受了一套 “商定的事实”,这是一份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谈判达成的文件。
看着判决的展开,安迪了解到,米洛迪和托伊尔认识了大约三个星期。

根据法庭听到的商定事实,在她死亡前的下午,他们发生了争吵。托伊尔将Mhelody赶出了他的单位,并去了当地的一个酒吧。
当他下午5点回来时,Mhelody还在那里。法庭听说这对夫妇和好后去了另一家酒吧,在那里他们喝了酒,然后在晚上9点回到托耶的单位。
他们在睡觉前继续喝酒。根据商定的事实,Mhelody当晚处于健康和交流的状态。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醒了,开始做爱,托耶开始掐住梅洛迪的脖子。
法庭听说这是米洛迪在早先的一次性接触中开始的现有做法,当时她将托耶的手放在她的脖子上。
托伊尔说,他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但当她希望他释放对她脖子的压力时,米洛迪通常会拍打他的手臂。这一次她没有拍打。
法庭听到,托耶在上午8:01打电话给triple-0,告诉操作员他一直在进行心肺复苏。
救护人员到达时,Mhelody已经没有了呼吸。第二天,即2019年9月22日,她在医院去世。
当安迪坐在那里听的时候,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有几件事情他觉得不对劲。
首先,他们在一起时,米洛迪从不饮酒。安迪想知道为什么她和托耶在一起时表现得如此不同。
“在我和Mhelody的关系中,从来没有谈论过窒息或其他类似的事情,”他说。
安迪承认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关系,与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但他认为在法庭上对Mhelody的描述听起来不符合特征。
托伊尔最初被授予强化惩戒令,这意味着他不必在监狱服刑。
然后,法官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判处的刑罚在新州不适用于过失杀人。
托耶被重新判处22个月监禁,12个月不得假释,但法官对不允许他免除托耶的监禁时间表示 “相当遗憾”。
这个过程让安迪不确定该怎么想。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法庭听到的关于米洛迪死亡的信息中存在漏洞,引起了一些疑问。

在米洛迪被勒死前的几个小时,她的手机里发出了性暗示和贬低的信息。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安迪和Mhelody一直在讨论他寄给她的一张礼券。
然后在晚上7点13分,一条信息到了,只是说 “滚开”。安迪以前从未听过米洛迪骂人。
当天晚上,还从米洛迪的手机上给她在菲律宾的一个朋友发了一条信息,说 “让我看看你的小穴”。
然后在晚上10:30至11:30之间,Mhelody的手机和Jay的兄弟Aaron*之间发出了一系列信息,将Mhelody描述为 “肮脏”,并说她有艾滋病毒。
在对警方的陈述中,亚伦称当晚还有几个视频电话来自米洛迪的手机。
在第一个视频通话中,一名男子接了电话。
据亚伦说,他起初很友好。然后在一次通话中,他突然大喊:”我已经毁了她,”他开始大喊:”我要让她感染艾滋病毒,我要再次毁了她的屁股。
亚伦告诉警方,他认为米洛迪看起来昏昏沉沉的,而且该男子曾试图拉下她的裤子。米洛迪推开了那名男子,并在自己身上拉了一件斗篷。
该男子随后威胁要再次强奸梅洛迪,然后挂断电话。亚伦在声明中没有指认该男子。
亚伦的母亲佩妮*和他的妹妹杰伊也说他们当晚在场,并目睹了视频通话。
“[他]说,他要继续强奸Mhel,他要让她得艾滋病。
“而且让我担心的是,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通常如果有人这样喊叫,他们就会动起来。”
在米洛迪死后,他们在新闻中看到了里安-托伊尔,并说他们认出他就是那个视频电话中的人。
佩妮和杰伊从未与警方交谈过,但他们知道亚伦已经做了正式的陈述,所以当他们得知法庭从未听说过这些电话时,感到非常震惊。
这意味着视频通话是否发生,从未被法院评估过。
护理人员在米洛迪被噎住的那天早上的日志显示,第一反应者在早上8点多到达里安-托耶的单位。
那是在托伊尔的三比零通话后的5分钟。
记录显示,当托耶在门口遇到救护人员时,他没有穿任何衣服。
救护人员无法从托耶那里得到任何关于他是否进行了心肺复苏的信息,因为他太激动和不安。
据医护人员说,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开始了心肺复苏。
救护人员在日志中写道:”病人被发现仰卧在地板上,衣着整齐”。
在法庭上听到的商定的事实陈述中,Mhelody在做爱时被掐住脖子,Toyer在意识到不对劲时立即打电话求助。
从未提及的是,根据记录,Mhelody被发现时衣着整齐,躺在地上。
这些记录以及医护人员向警方所作的陈述也从未成为证据。
由于托耶的听证会是为了决定他的过失杀人罪的判决,记录和护理人员的陈述从未被法院检验。
上午8点15分到达现场帮助抢救的一名医护人员观察到托伊尔在大喊:”请呼吸,我的生命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不敢相信这发生在我身上”。
这名医护人员注意到米洛迪有一颗松动的牙齿,几乎脱落了,而且她的牙龈周围似乎有创伤。他说,在汇报时,另外两名医护人员也注意到了这颗松动的牙齿。
在米洛迪被转移到医院后,医生和护士继续为她的最后一天做医疗笔记和记录。
一位医生指出,Mhelody的脖子下三分之一处有瘀伤。一名照顾Mhelody的护士注意到她的脊柱附近有一个7厘米的红色印记。
新州首席法医Isabel Brauwer博士在Mhelody在纽卡斯尔死亡约一周后进行的尸检并没有注意到Mhelody的脖子有任何瘀伤或痕迹。
布劳威尔博士指出,米洛迪的甲状腺软骨有骨折,但没有提到牙齿松动或她背上有7厘米的红印,这让人怀疑这些伤害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新州卫生部拒绝就Mhelody的尸检报告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表意见。
法院没有考虑尸检报告。
鲍勃-诺布尔警司负责瓦加瓦加警察局,在米洛迪死亡时,他是负责的警官。
他说,警方没有形成一个观点,即为什么法庭接受托耶在那天早上进行了心肺复苏,而护理人员认为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Mhelody,另一个是被告–所以我们在那件事上没有着落,”他说。
诺布尔警司说,警方有兴趣了解Mhelody被发现时穿戴整齐,但 “最终向法庭提出的说法是他们在那天早上进行了性行为”。
“我的意思是这两件事,它们似乎是不一致的,但我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诺布尔警司说。
“你只需允许,首先,调查人员审问所有这些事项,然后显然是由法院将所有这些加起来。”
他说他不能谈论米洛迪的朋友报告的视频电话,但他坚称警方进行了彻底调查。
“最终你只能证明你能证明的东西,你不能证明证据不能证实的东西,”他说。
“作为一个普通人,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最终检察官,以及在本案中,法官大人,必须作出结论和判决,而那些在人们心中可能难以调和的不方便的信息并不一定构成不同结论的理由。”
新州检察长办公室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发表声明,称其不能讨论未在法庭程序中引用的材料。
ODPP说,它已经 “对警方简报中的每项证据的法医价值形成了看法”,以及这些证据是否与判刑听证会相关并可被接受。
但是,会导致更高的刑罚的证据必须由 “控方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确定”,”对某一问题的怀疑是不够的”。
里安-托耶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的律师扎克-坦卡德也拒绝接受采访。他的大律师马克-丹尼斯没有回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惠利说,在量刑听证会上听到的证据通常比审判少得多,但他认为法院应该被告知视频通话的情况。
“他说:”你有一幅由商定的事实所描绘的画面,这或多或少是一对幸福的夫妇,晚上要睡觉了,他们可能喝得有点多,但他们或多或少是幸福的,并自由交流。
但亚伦的声明描绘了 “一个完全不同的、相当可怕的关系图景,一个被敌意和攻击性所困扰的关系”,他说。
这位退休法官说,这些遗漏很重要,让人对司法程序产生怀疑。
米洛迪的母亲阿维利娜-布鲁诺在女儿死后三天得知她的死讯,当时澳大利亚警方在马尼拉追踪到了米洛迪的哥哥。
这个消息让人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法律程序让阿维利娜难以理解。
“布鲁诺女士说:”判决是如此之低,仿佛没有人被杀。
“如果[Mhelody]没有去[澳大利亚],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她的死亡也不会发生,我们会一直幸福到现在,即使我们很穷。”
请听背景简报的完整播客调查 “她的名字是米洛迪-布鲁诺”。
*为保护某些消息来源的身份,名字已被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