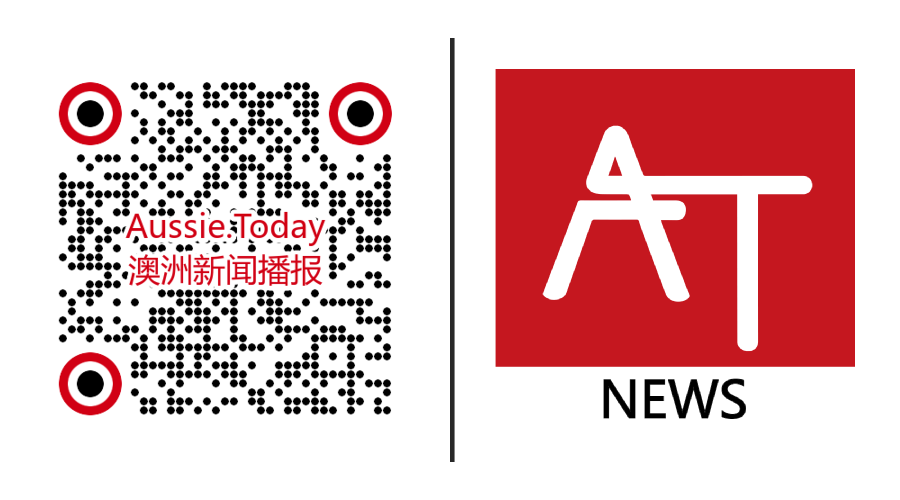2019年8月4日,玛丽-比塞尔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名叫奥兹的健康女孩,她立刻知道这个孩子将是她的整个世界。
第二天,玛丽又去工作了。
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新墨西哥州里奥兰乔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她在孕检呈阳性后不久发现,这所学校不提供任何带薪育儿假。
在让他们的病假滚动的十年中,这对夫妇已经积攒了12周的带薪休假。
他们本可以在奥兹出生后利用这段时间,但由于大流行病肆虐,他们决定把时间留到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会坐在沙发上,拿着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只是在她尖叫的时候交换着抱她。玛丽说:”我正在哺乳,在上课时抽水……这并不容易。

“但感觉我们很幸运。我的意思是,大流行病是可怕的。我不敢相信我会这么说,但这对我们来说很了不起。
果然,当学校董事会投票决定将一些教师送回教室时,他们的策略得到了回报,不需要接种疫苗。他们开始请假,以节省日托费用,并避免让新生儿接触到病毒。
说到请假,玛丽的故事并不完全罕见。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一有全职工作的母亲在产后不到10天就返回工作岗位。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带薪休假的联邦保障。它是唯一没有这种政策的富裕国家,而是提供无薪假期–主要照顾者的12周。
将美国中产阶级作为竞选重点的总统乔-拜登,正试图在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改变这种状况。

但由于要克服几十年的政治停滞,美国人并不感到乐观。
“为了这个小小的生物,你的整个生活被连根拔起,这已经是很难了,”玛丽说。
为了代替国家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私人雇主已经开始超越联邦政策,提供某种版本的带薪育儿假。
这包括美国政府本身。
2019年,当时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政策,给予所有210万联邦工作人员12周的带薪假期。还有九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提供某种带薪休假政策。
但是,全国仍然只有一小部分工人–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大约有21%的人可以享受任何形式的带薪休假。
拜登先生在上任后不到三个月就提出立法,使所有工人都能享受长达12周的带薪家事假,每月最高可享受4000元(5380元)。
该政策需要10年才能生效,适用于母亲和父亲,或任何寻求时间来照顾亲人的人,包括因病。
一项又一项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普遍赞成这样的带薪休假政策。
这种支持在各政治派别中都有,而且在大流行期间,政府颁布了紧急病假政策,这种支持只会增加。
但美国人–尤其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任何带有加税的政策都心存疑虑,即使像拜登先生承诺的那样,只针对最高收入者。
总统最初提议将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率从37%提高到39.6%,并收紧资本收益税条款,削减逃税行为。
但他已经表明,在共和党人对税收举措提出批评后,他对谈判持开放态度。
毕竟,加税最终是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支持在2015年最后一次认真推动带薪休假的原因。

当萨曼莎-温特林在2013年有了她的第一个女儿时,她还在从事一份她已经厌倦的地方政府工作。

她坚持工作是因为她已经积累了近三个月的假期和病假,她可以用这些假期来补充所提供的五天带薪产假。
但当她回到办公室时,她所工作的民选官员已经离开,这意味着她的工作也没有了,而他们提供给她的角色将是一个严重的降级。
她求助于同时做一连串的兼职工作,但她的工资几乎无法支付照顾孩子的费用。
“感觉你没有办法赢。如果你辞掉工作,你就没有野心。如果你不工作,你就是在向社会乞讨。如果你不照顾自己的孩子,你就是一个坏妈妈。”她说。
“他们只是告诉你要吸吮它。
当萨曼莎在2019年生下她的第二个孩子时,她已经放弃了她的梦想职业道路,参加了一些研究生课程,并在一个非营利组织找到了一个行政职务,提供三周的带薪产假。
像玛丽一样,她很幸运,大流行病正好在她的假期结束时发生,这意味着她可以在家里和她的新生儿呆得更久,即使这意味着要做很多多任务。
“人们会说这样的话:’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你应该节省’,”她说。
“但你如何为家庭这样的事情做计划?这只是很多艰难的选择。”
艰难的选择的数量随着妇女参与美国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这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美国只通过了一项休假政策。
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唯一不保证带薪休假的国家。但不久前,澳大利亚还处于同样的境地。
2009年和2012年,议会通过法律,规定新生儿或新收养儿童的主要照顾者享有18周的带薪休假,并按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墨尔本RMIT大学的性别经济学家Leonora Risse说:”是政治环境造成了差异,”她的研究涵盖了这两个国家。
鉴于经济学家已经能够观察到哪些措施在其他国家最有效,美国的延迟可能会被证明在广泛的范围内有帮助。
“里瑟博士说:”我从拜登的提案中读到的是一种意识,即需要采取一种全面的方法。
“在澳大利亚,事情要零散得多”。
拜登先生提议的休假政策只是被包裹在一个名为 “美国家庭计划 “的巨大综合法案中的几个之一。
按照美国的政治标准,该法案被认为是疯狂的进步,因为它提出了两年免费的学前教育、两年免费的社区大学和为低收入家庭减税等建议。
它不太可能在国会上院获得通过,共和党人在国会100个席位中拥有50个席位,但大多数法案需要60票才能通过。
白宫估计,该法案将为家庭每年节省超过15,000元的开支,但它为联邦政府带来了高达1.8万亿元的价格标签。
而且,这也只是一项可能耗资2.2万亿元的基础设施计划的后半部分。
将这两项计划捆绑在一起的尝试给辩论增加了另一个意识形态层面,导致右翼政客问道,使拥有家庭更容易是否断然等同于使美国的桥梁和公路更容易通行。
如果美国人开始把这两样东西看作是强劲经济所必需的,这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先例?
对于一些妇女来说,生孩子的费用根本无法承受。
有了一个孩子之后,瑞秋已经排除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面临几十年的债务,”这位来自马里兰州的母亲说,出于政治考虑,她要求我们不要公布她的姓氏。
“即使是日托,这里每个月也要2000元。这和我的抵押贷款规模差不多。”
经济因素只是出生率下降到替代率以下并继续下降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生育率在2020年创下42年来的新低,平均每名妇女生育1.7个孩子。
在澳大利亚,即使在获得带薪休假的十年之后,2019年的比率也同样创下了每名妇女1.66个孩子的最低纪录。
选择和环境不能被解析出来,但我们确实知道,这两个国家都看到了非经济因素的趋势,比如推迟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孩子对个人的成就感不是必须的。
在美国,关于出生率下降的最新报告带着支持生育主义的暗流进入政治辩论。
学者和政治家们指出,如果不能在经济上支持美国家庭,可能会产生另一个后果。削弱美国的全球整体实力。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哈德-曼朱(Farhad Manjoo)写道:”世界上的美国人可能已经不多了–最关键的是,明天的工作年龄、生孩子、产生想法、建设社区的美国年轻人。
“增长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需要–不仅仅是我们能负担得起更多的人,可能是我们不能不负担。”
Risse博士说,这种情绪可能会使家庭政策有倒退的危险,因为它把养育子女作为妇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但它也可能会引起投票反对拜登先生的大家庭计划的政党的共鸣。毕竟,共和党人以 “美国优先 “的言论而闻名。
美国人会告诉你,政治辩论有时会让人感觉到大局观,以数字为导向,以解决方案为重点,从而忽略了生活在这里的混乱、细微的生活体验。
“对我来说,这似乎只是归结于谁在管理国家的角度,”克里斯-比斯特林-博尼利亚在给她的第三个孩子,一个六周大的新生儿打嗝时说。
“他们无法与这些问题产生个人联系,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支持任何改变呢?”
Chrissy认为她梦想中的大学讲师工作可能与做母亲兼容,部分原因是暑假的好处。
她还在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时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并将一切计划得很完美,在她的暑假开始时就进入了分娩状态。但是她的第二个孩子来得更棘手,就在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
在她怀孕期间,她不仅管理她丈夫的绘画业务,还担任他的律师。她为他完成了成为美国居民的文书工作,这涉及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前往墨西哥。
而当孩子出生后,她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担任了一个学术主管的角色,提供在家工作的灵活性,这样她就不会在育儿上浪费钱。
她几乎一直全职工作。她为竞争激烈的学术工作市场完成了17次面试。她写她的论文。而她每晚可能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所有这些使她获得了美国学术界最令人羡慕的角色–一个有福利和相对工作保障的全职教授职位。但是在她搬到科罗拉多开始工作的两天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她意识到,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她不可能有能力保持这份工作。她可以通过管理她丈夫的生意赚更多的钱,节省照顾孩子的费用。
因此,她放弃了她长期以来为之努力的东西。她辞去了她的梦想工作。
“她说:”我的朋友喜欢开玩笑说我在混乱中茁壮成长。
“但它也只是事情的方式。它就是这样。”